2012年12月14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985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承办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度论坛“新政与民生:谁来养活中国老人”在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隆重举行。会议由封进教授主持,郑秉文、方汉明、王丰、袁志刚四位学者先后就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各抒己见,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封进与何立新对几位学者的演讲进行了评论。
封进教授首先对本次论坛的选题背景和主要议题做了介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约占总人口的16%;2020年达到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8%。未来我们需要多少资源去养老?与此同时,尽管政府在老年保障体系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建设性工作,但现状仍然令人不安,我们用什么去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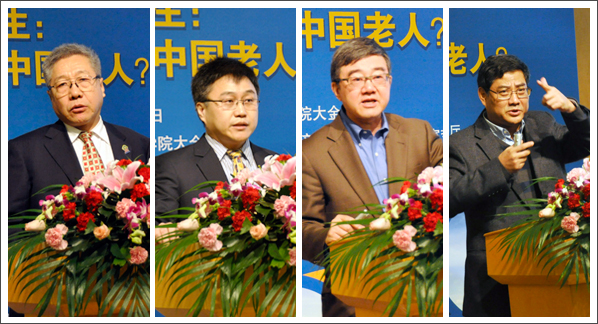
郑秉文教授对中国近年来社会保障系统的改革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梳理。
首先,在养老金的投资方面,中国如何在养老金基金规模高速增长、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双高”环境下,中国的养老金投资应逐渐展开一系列投资体制的改革,允许更多元的投资。投资收益是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一种制度创新,他可以减轻你的后代由于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在97年创造的一种制度,让养老金缴费率每年提高0.1到0.5左右,一直从97年的6.85提高到03年的9.9,开始保持不变。根据测算,这样的改革使养老金缴费率到2034年都可以持平于9.9。而如果97年开始没有改革,2034年的缴费率将达到15。在养老金投资的安全性上,郑秉文教授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进行投资限制;二,用余额进行投资;三,可以进行绿色投资、股权投资、向新兴市场投资。
在退休年龄的话题上,郑秉文教授认为,他从一个研究学者来说,主张应该提高退休年龄。一个国家的进步,应当仰赖于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任何一种制度对于劳动力的供给都有扭曲,中国应当选择一种与国家的容忍程度相匹配的制度。
在债务的争论上,郑秉文教授认为,马骏与曹远征等经济学家测算得出的18.4万亿养老金债务缺口,是正确的。首先,中国有许多省份当期已经收不抵支;其次,中国的统筹基金还存在许多隐形债务;第三,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具有保输不保赢的性质,账务未领取完毕可以继承,如果超出了平均余命,则可多受益。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很可能是无法做实的。
郑秉文教授最后提到,根据2012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现的这些争论,有几点启发:第一,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困难之一在于,受到了许多网络声音的牵制;第二,中国养老金的改革缺乏顶层设计。第三,在网络时代,中国的政府需要防止民粹主义,让制度改革成为可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改革是唯一出路,改革方向是需要设计的,且不是看网络。
方汉明教授的演讲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险上。首先,他从收入、风险等角度厘清了为什么老年人更加需要保险。在设计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时,也要从这些角度,首先进行顶层设计。一个保赢的制度,不属于保险。
在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上,包括几个部分:医疗保险的付费体系、医疗服务的提供体系、管理体系。在医疗保险体系中,需要统筹考虑这些问题。方汉明教授介绍了一些主要OECD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有全民医疗保险,13个国家自动提供医疗保险,10个国家要求强制购买医疗保险,但在医疗保险提供者的所有制度上略有不同。美国2011年的医疗改革实上跟荷兰、瑞士是很接近的,也要建立一个私立的医疗保险市场。
当前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其一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依赖率为30%,中国此时已经达到38%。这将导致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无法维持。其次是道德风险的问题,这些制度会扭曲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在1960年之后美国建立了提前退休制度,这就使美国在62岁上出现了一个退休率高峰。在医疗方面,医疗保险一方面让大家规避医疗支出风险,另外一方面,导致大家过渡消费医疗服务,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可能导致医疗保险支出过度。
方汉明教授提到,在美国医改中,一个较为热门的问题是将医疗保险改革为天灾保险,只保大灾,这可以让病人关注实际医疗价格,而不是实际支出。他可以抵抗大的风险,也可以消除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异。医疗保险的改革是一个一揽子设计,必须在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中找到平衡,寻找最优的系统设计。
方汉明教授最后认为,提高退休年龄是必然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减小制度的扭曲激励,通过提高积极性的方式延长老年人的工作年限,是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中国需要从西方国家中得到借鉴,取其精华,确定中国接下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取向。
会议的第二部分的第一位主讲人是王丰教授。王丰教授主要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
第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了?王丰教授认为,当前的高层领导对于这个问题也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不同的统计口径下,2030年的劳动力预测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用一个比较合理的纳税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口径——20到59岁来计算,中国在2030年的劳动力从之前估计的9亿降低到了7.5亿。在人口数量之外,劳动人口和老年人的比例在当前是5:1,而在2030年只有2:1。这需要我们对人口有更高的忧患意识。
第二,王丰教授阐述了人口红利的性质。首先,人口红利来源于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之间的差异,人口红利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上只能经历一次,是不可重复的。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就是要将中间部分的生产,给填补到两头没有生产,纯粹消费的周期中。中国人口红利变化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年—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这种计算方式是比较保守的,有的说法是25%都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第二阶段是2000—2013年,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这个阶段,贡献减少至消失。第三阶段:2013年—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从2013年开始,中国情况和其他的几个经济体没有太大的优势,比美国、法国还差很多,如果经济增长率15%,将近十分之一的经济增长率会被人口红利负的吃掉。这只是保守计算,因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率也可能会下降。林毅夫认为,日本、台湾在达到美国人均收入四分之一的时候,还有30年的增长,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人口的变化。中国人口情况和那个时候的日本、台湾面临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其次,随着经济的变化,劳动力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带来的边际收益,也远远小于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边际收益。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有许多特点。首先是速度快。中国65岁老人比例从9%上升到25%所花的时间,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其次是家庭的脆弱性,在计划生育下,大部分家庭的老人退休时只能大部分仰赖于退休金收入。
最后,王丰教授简要介绍了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机会在于,中国年轻人口中的高教育人口比例可能会提高平均的人力资本。而挑战在于,中国老年人口的未来花费可能还会增大。这些都会对对中国的未来养老体系提出新的挑战。
袁志刚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人口老龄化与金融。袁志刚教授认为,子女实际上是中国家庭最好的金融产品。而在计划生育下,子女这一金融产品的投资被认为地限制了,这要求政府尽快地改善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50、60年代的父母虽然没有储蓄,但是他们的多个子女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但这一代父母没有了子女,如果他们的储蓄仍然被消费所掏空,他们的老年生活就会有水平大幅度下降的风险。因此,这有可能倒逼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让中国在计划生育的情况下,可以迅速跟上美国、欧洲的很好的金融体系,并且让实体经济走向世界,将资本,跟印度、越南这些年轻人充分的国家去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解决一部分养老,至少部分弥补养老的缺口。袁志刚教授认为,这说明了中国今天的金融体制的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袁志刚教授提到,在欧美国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其金融抑制程度越低,且FDI越高。这说明老龄化的国家需要更强大的金融市场,资本也更加需要走向海外。
然而,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不完善,大量的储蓄、外汇储备,在投资了美国债券之后,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借长贷短的陷阱,在长期来说反而是债务人。这对于养老和金融之间的联系十分不利。其次,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并不好。在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最强的企业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仅有五席。如何靠这样的金融市场和企业为中国的未来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袁志刚教授最后提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尽可能减少对主板市场、股票市场的依赖,大力发展为实体经济的股权交易,尽可能少让政府直接插手。金融业打破政府垄断,才能真正做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让这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更加有希望。

最后,台上四位教授、两位评论人与台下的同学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大家就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扭曲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各位老师与同学都感到受益匪浅。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